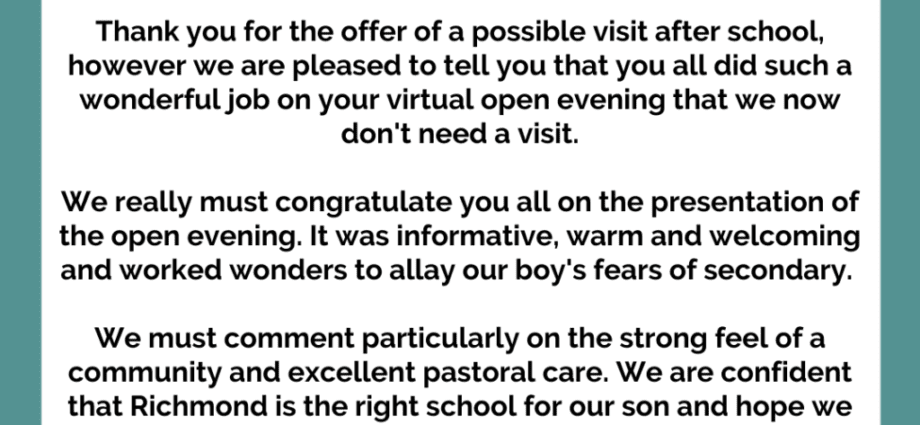“我的女儿认为我们生来是白人,长大后就变黑了……”
42 岁的 Maryam 和 10 岁的 Paloma 的证词
我表弟去世后,我收养了帕洛玛。 帕洛玛那时才 3 岁多一点。 小时候,她以为你生来是白人,长大了就变黑了。 她确信她的皮肤以后会和我的一样。 当我向她解释事实并非如此时,她非常失望。 我告诉他异族通婚,我的父母,我们的家庭,他的历史。 她非常了解。 有一天她告诉我 “我可能外表是白色的,但我的内心是黑色的。” 最近,她告诉我“重要的是内心是什么”. 势不可挡!
像所有小女孩一样,她想要她没有的东西。 帕洛玛有一头直发,梦想有辫子、附加物、蓬松的头发“像云一样”,就像我有一段时间的非洲发型一样。 她觉得我的鼻子很漂亮。 从她的说话方式,从她的表情来看,她和我很像。 夏天晒黑了,我们把她当作混血儿,人们认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的情况并不少见!
我们在马赛安顿下来,我在那里寻找一所适合其需求的学校,以适应其相当厚重的历史。 她在一所多元化的学校里,采用 Freinet 教学法,学习适合每个孩子,班级按双层组织,孩子们得到授权,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独立学习。 . 它符合我给他的教育,它使我与学校调和,我个人讨厌学校。 一切都很顺利,她和各行各业的孩子在一起。 但我为她上大学做了一点准备,为可能向她提出的问题,为她可能听到的思考做准备。
有很多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,关于肤色如何决定一个人将如何被对待. 我告诉她,作为一个黑人妈妈,也许我会受到不同的看待。 我们谈论一切,殖民主义、乔治·弗洛伊德、生态……对我来说,向他解释一切很重要,没有禁忌。 我对帕洛玛的经历与我对白人母亲的经历完全不同。 她必须一直走到前线,为我辩护,面对种族主义思想。 今天,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帕洛玛的皮肤较浅,是不是因为我的六英尺和我的光头强加了它,这是值得尊重的,如果是因为马赛的多样性,但它进展得很好。 “
“与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相比,我觉得这对我的孩子来说更容易。 “
皮埃尔的证词,37 岁,Lino 的父亲,13 岁,Numa,10 岁和 Rita,8 岁
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人们总是认为我是被收养的。 总是有必要解释我确实是我父亲的儿子,因为他是白人。 当我们一起去购物时,我父亲必须通过指定我陪同他来证明我的存在。 人们在商店里跟着我或斜眼看我的情况并不少见。 当我们去巴西时,我母亲来自那里,我父亲不得不再次证明我们的出身。 这很累。 我在一个相当富裕的环境中长大,并不是真正的混血儿。 在我的学校里,我经常是唯一的黑人。 我听到了很多相当边缘的言论,中间夹杂着“哦,但是你,不一样”。 我是个例外,这些言论应该被视为一种恭维。 我经常开玩笑地说,有时我有一种“假”的印象,是黑体中的白。
我的印象是我的孩子们,三个小金发女郎! 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种收养推定并不过分。 人们可能会感到惊讶,他们可能会说“嘿,他们看起来不一样”,但仅此而已。 当我们一起在路边咖啡馆时,我真的感受到了好奇的表情,其中一个人叫我爸爸。 但这反而让我发笑。 我也玩它:我得知我的大儿子在学校被打扰了。 大学毕业的一天,我去接他。 对我的黑人,我的纹身,我的戒指,它产生了影响。 从那以后,孩子们就让他一个人呆着。 最近,当我去游泳池接他时,Lino 告诉我:“我相信他们会把你当作我的管家或司机”。 暗示:这些种族主义白痴。 当时我并没有太大反应,这是他第一次告诉我这样的事情,这让我很惊讶。 他必须在学校或其他地方听到一些事情,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主题,一个他关心的问题。
我的另外两个孩子确信他们是混血儿,就像我一样,而他们是金发碧眼的,而且相当公平! 他们与巴西文化息息相关,他们想说葡萄牙语并花时间跳舞,尤其是我的女儿。 对他们来说,巴西就是狂欢节,音乐、舞蹈无时无刻不在。 他们并没有完全错……尤其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我妈妈到处跳舞,甚至在厨房里。 所以我试着把这种双重遗产传给他们,教他们葡萄牙语。 今年夏天我们应该去巴西,但大流行已经过去了。 这次旅行仍然在计划中。 “
“我必须学习如何为我女儿的头发定型。 “
Frédérique 的证词,46 岁,Fleur 的母亲,13 岁。
我在伦敦生活了二十多年,芙蓉出生在那里。 她的父亲是英国和苏格兰的混血儿,来自圣卢西亚,有加勒比血统。 所以我必须学习如何为我的小女孩的自然头发定型。 不容易 ! 一开始,我测试了产品来滋养和解开它们,这些产品并不总是很合适。 我向我的黑人朋友征求意见,我还咨询了附近的专卖店,以了解在这种头发上使用哪些产品。 我承认,我也不得不像许多父母一样即兴创作。 今天,她有她的习惯,她的产品,她自己做头发。
我们住在伦敦的一个地区,那里有多种文化和宗教。 Fleur 的学校在社会和文化上都非常混杂。 我女儿最好的朋友是日本人、苏格兰人、加勒比人和英国人。 他们互相取食,发现彼此的特色菜。 我在这里从未对我的女儿感到种族主义。 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的混合,我的社区或所做的努力,也在学校。 每年,在“黑人历史月”之际,学生们从小学开始学习奴隶制、黑人作家的作品和生活、歌曲。 今年,大英帝国和英国殖民在节目中,一个让我女儿反感的话题!
随着“黑人的命也是命”运动,芙蓉被这个消息震惊了。 她画了一些画来支持这场运动,她感到很担心。 我们在家里经常谈论它,我的搭档也非常关心这些问题。
正是在我们往返法国的旅行中,我目睹了关于我女儿的种族主义思想,但幸运的是,这只是轶事。 最近,芙蓉震惊地在一个家庭中看到一个黑色新郎的大型雕像,处于仆人模式,戴着白手套。 她问我家里有这个是否正常。 不,不是真的,它总是让我很生气。 有人告诉我,这种装饰可能很流行,不一定是恶意或种族主义。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觉得很有说服力的论点,但我还不敢直面这个话题。 或许芙蓉敢,以后……”
西多妮·西格里斯特的采访